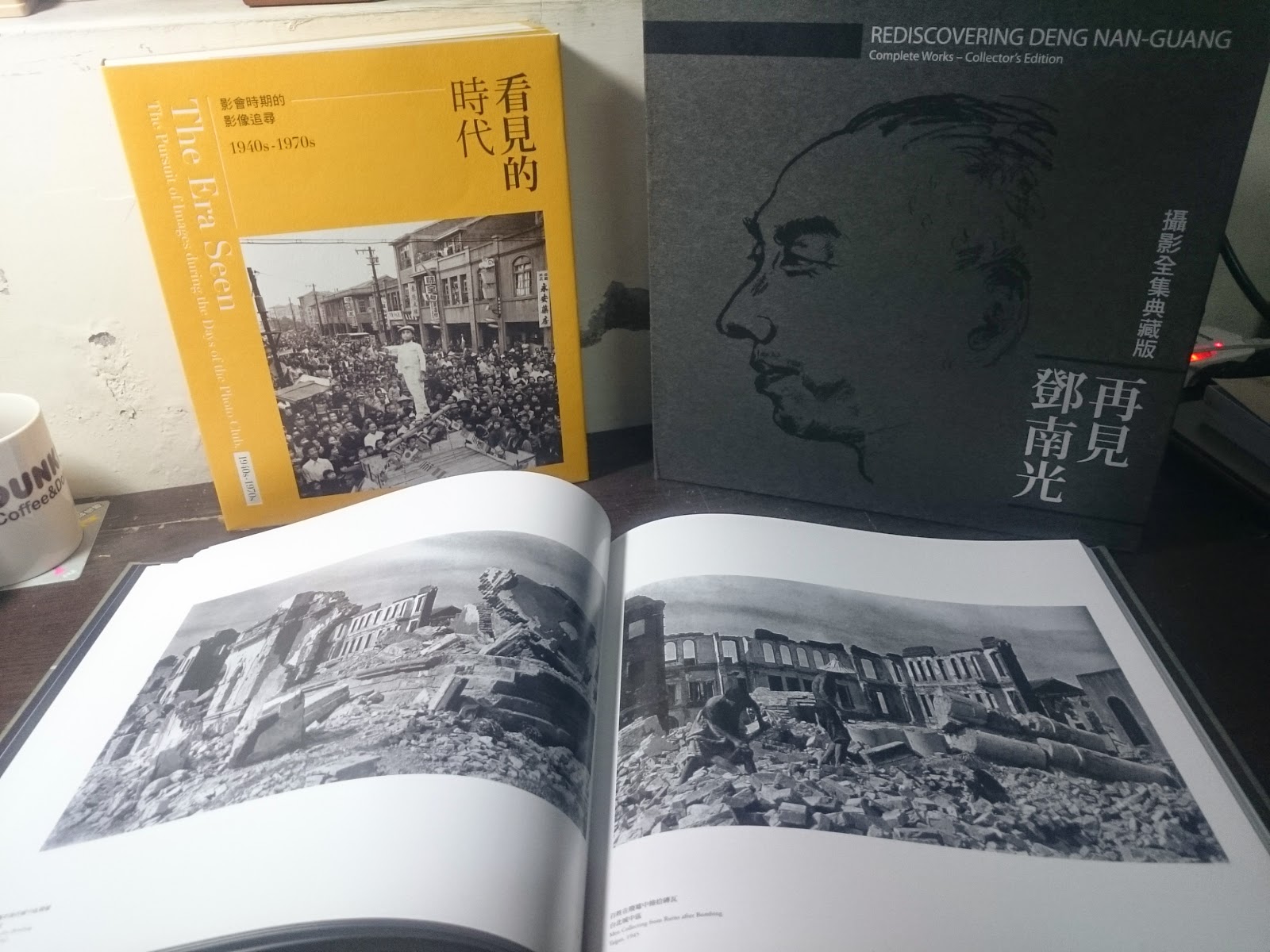寫在前面
這篇文章草成於11月23日,投過想想論壇與獨立評論@天下都未獲採用。我想應該都是文章太過於長,乃至已經沒有時間性的緣故(當然,也可能是體例問題)。這篇文章仍不算成熟,但應該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面向。因此還是不揣淺陋,刊載在自己的部落格上。一些問題可以參考附記與寫在後面。
一、
趙衍慶,一位默默無名的臺北市長參選人,卻因為自身的過往,捲入一陣風暴。事件起於博士生江昺崙在想想論壇發表了一篇〈200萬說一個故事:78歲台北市長候選人趙衍慶〉,憑藉著片段的資訊,主觀地將趙先生的從軍經驗,認定為是713事件中被強抓從軍,這篇文章隨後在網路上廣為傳播。有幸為曾專訪過趙先生的許和鈞、許劍虹等人見得,提出了指正批評。如果當初江先生更加謹慎些,留意到趙先生曾經參選過2009年的立法委員補選,也看到選舉公報上刊載了解放軍經歷的話,這樣的張冠李戴也就不會發生。
但兩位許先生的一些批評,卻令人感到困惑。兩位都認為,這篇文章是為了攻擊某陣營而杜撰。仔細閱讀江文,卻很難發現這樣的企圖。也許,兩位先生一時不察,將網友們對這篇文章的解讀,誤加在江先生身上。
更令筆者不解的,是許和鈞先生的批評。在許先生的看法裡,似乎「無訪問過本人,又無任何史學背景」的人,不能夠討論一個人的過去,而許先生更進一步批評:「江昺崙先生請別把你文學的那套幻想,拿到要求嚴謹查實的史學上來用好嗎?」忝為一名史學研究生,對這樣的言論卻是感到相當不安。這似乎是在說:歷史學與直接的訪談,才能夠接近,甚至擁有真實。而也只有握有真實,才握有歷史的發語權。
我感到很不安。
因為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無權壟斷歷史的事實與詮釋。
而面向遼闊深邃的過去,我們看到的,卻常是往事如煙。
二、
誤打誤撞,趙衍慶的過往掀起了波濤。而另外兩位參選人:柯文哲與連勝文的父祖,自選戰開始以來,始終成為兩方人馬互相攻擊的對象。
幾天前,連勝文之父連戰,攻擊柯文哲是「青山文哲」。其用意,恐怕是攻擊柯文哲為日人之後,對國家不忠,又或者,更惡毒與切確的,是如郝柏村指稱的「皇民」之後:看似忠誠,實則潛伏異心。消息一出,人們不免想起連家先祖連橫與臺灣總督府之間有著怎麼樣的曖昧關係。而最為尷尬的,恐怕便是1930年的鴉片特許事件。那一年3月2日,正當民眾黨人對總督府的〈鴉片改正令〉而激烈批評時,連橫卻在總督府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了後來被稱為「新阿片政策謳歌論」的文章,為當時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辯護。此文一出,引致臺灣知識界譁然。當時作為民族運動要角的林獻堂,也在日記中記下了此事:
三日(案:應為二日)連雅堂曾在《台日》報上發表一篇,說荷蘭時代阿片則入臺灣,當時我先民移殖於臺灣也,臺灣有一種瘴癘之氣,觸者輒死,若吸阿片者則不死,臺灣得以開闢至於今日之盛,皆阿片之力也。故吸阿片者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步也。末云僅發給新特許二萬五千人,又何議論沸騰若是?昨日槐庭來書,痛罵其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請余與幼春、錫祺商量,將他除櫟社社員之名義。余四時餘往商之幼春,他亦表贊成。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6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櫟社成立於1902年,是當時臺灣重要的詩社之一,許多民族運動的領袖也參與其中。此後一個月,林獻堂便為此事與一些櫟社友人討論。最後,在4月2日櫟社總會上,決議將連橫除名:
午後往津梁處,囑汝南修書與錫祺社長,商雅堂除名之事。四時幼春亦來,言將槐庭之書發表,就中有趨媚外人之語,改作貽笑外人何如?余亦以為然。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7日)
午後伊若來,招之同往幼春處,商修書致錫祺社長召集理事會,以解決雅堂除名之事。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8日)
昨日槐庭來,宿於津梁處。九時餘來訪,余招之同往萊園散步。十二時錫祺、子瑜、了庵、子昭來,而伊若、汝南亦至。午餐後同到幼春處開櫟社理事會議除名連雅堂,而棟梁亦來,乃改理事會為總會。槐庭再提議雅堂於三月二日在《台日》紙發表阿片意見書云云,非將他除名不可。余問社則除名之條,錫祺謂有違背本社規則及污損本社名譽者除名。子瑜謂如其意見書,未必有污損本社名譽,萬一因此以致訴訟亦未知,須要慎重,幼春、錫祺、了庵、子昭皆贊成其說。余謂誣衊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伊若、汝南贊成余說。棟梁謂此係政見不合,若欲除名,請待他日。議論結果,決定認他不熱心於本社,作為退社決議錄,棟梁不蓋印。三時餘接一匿名信言理事中吸阿片煙者過半數、有非孝論者、有公益會主腦者、有同姓結婚者,此不革除,此獨對於連某不留餘地,竊為諸公不取。幼春特別憤慨社員中有受人嗾使之鷹犬。夜受津梁之招待,錫祺、子瑜、了庵、棟梁、子昭返台中。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13日)
繼開櫟社總會。先議收支決算;次議雅堂,不將其三月二日之阿片論文為之除名,而用十六回不出席,認其退社;余提議子瑾拐誘同姓女子,亦當除名,討論後投票,決定認作退社。七時受幼春之招待共飲喜酒,幼春率子婦行禮,晏臣為來賓總代,述謝辭。席散歸宅作擊鉢吟,題曰「泉筆」,支韻七絕。余倦甚,僅作一首。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4月2日)
將連雅堂除名的這一天,是林幼春長男林培英與鹿港施家施璇璣結婚的日子,櫟社成員們先是出席了結婚典禮,隨後又召開總會,議處了連雅堂除名之事。從林獻堂的日記看得出來,除名一事是否得當,在櫟社內部不是沒有爭議。畢竟以民族立場而言,櫟社中人有親日的公益會主腦;就倫理立場而言,亦有違背同姓婚習俗者。更不要說櫟社理事中不乏癮君子了。但最後,眾人仍然以缺席多次,議決連橫除名。同為櫟社成員的張麗俊,也記下了這次會議:
我等櫟社友十餘人仍回獻堂家開櫟社會議,幼春因忙,棟樑、上花先歸,三人不與。社長報告昭和四年度收支決算濟,方提議台北連雅堂自大正十二年竪〔豎〕櫟社碑來出席至今,多年俱欠席,照社規三回欠席者退社,又兼為阿片新許可事件,有礙社規,退社議決;又棟樑前欲左坦〔袒〕雅堂,反對本社,亦欲議決退社,嗣因對幼春懇求寬諒,幼春對社長通過,因暫按下。獻堂提議林子瑾渡華多年,諒無再回臺之日亦當退社,子瑜、聯玉二人意欲保留,因各投票採決退社。又提議招加入新社員以繼續此社,獻堂將其一子、幼春將其二子、子瑜將其一女入社,眾皆承諾,候後回定決。又參議本社三十周年欲鑄鐘記姓名為永遠記念,議尚未決,幼春令人來邀赴新婚晚宴,因將此案保留,此初十日到子瑜東山踏青會再議。一行十餘人仍到大花廳赴盛大晚宴。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30年4月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不過,今天人們之所以知曉此事,並不是來自這些近年方公開的日記,而多半是來自吳濁流的回憶錄《臺灣連翹》。在書中,吳濁流陳述道:當時民眾黨等人反對臺灣總督府的〈改正鴉片令〉,找了國際聯盟的調查員來臺。總督府為了掩飾醜行,於是以三百圓收買了連雅堂。此文一出,「引來喧天動地的責難,臺灣人知識階層對他深深失望」,不僅櫟社將其開除,連帶臺灣民報預定採用的連震東,也因之遭到拒絕。父子倆只好往親日的《昭和新報》去。到了戰後,連橫卻搖身一變為抗日大詩人,大學者,連兒孫都沐其餘蔭。吳濁流略帶嘲諷地說:「這也算是臺灣七大奇觀之一吧。」
吳濁流當時是新竹州四湖公學校的訓導,與這些民族運動者乃至連雅堂本人,多沒有直接的往來。是以他所知曉的,未必真確。但,連家自己的說法又是如何呢?戰後鄭喜夫編寫的連雅堂年譜中,出現了連震東口述的說法。連震東表示,那是因為他留學有成回臺,林獻堂將延其為《臺灣民報》記者,但該社幹部、記者如謝春木等忌妒他中、日文並佳,恨相形見絀,所以力為阻擾。遂有好事者假連橫之名,意欲阻擋其入《臺灣民報》。
從林獻堂日記看來,連震東入民報社,是由父連雅堂請求,林獻堂應允說項之事。而在該文刊出後,連氏父子仍多次拜訪林獻堂,其中幾次便是為了連震東入報社事而來。當年3月20日林獻堂在臺北時,連氏父子便曾前去拜訪,盼勿因鴉片一文而影響連震東入報社。林獻堂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雅棠〔堂〕、震東來訪,謂為二日《台日》紙發表其阿片意見書,而民報社因此之故,以致不採用震東。余謂父善子未必善,父惡子亦未必惡,舜之殛鯀也,興禹,此古人最好之例也,請少待,俟余詢問,然後定著。
十時餘萬俥來,余問其採用震東之事。他言春木、郭發等反對,因而躊踟〔躇〕。余謂震東頗可造就,切不可因其父而棄之;萬俥謂震東性質恐與春木等不合,余謂若然當再斟酌。遂與資彬同到大正町四條通萬俥之宅午餐。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20日)
第二天,林獻堂出席蓬萊閣新民報社宴席,連橫亦在席間。連橫又曾於7月1日拜訪林獻堂,不過日記中並沒有記載所為何事。至於連震東,也在3月31日再次拜訪林獻堂,詢問任職一事。林獻堂記曰:「連震東來問民報社欲採用他否,頗出誇口無禮之言。」三個月後,連震東復於6月30日拜訪林獻堂,日記中云:「三時餘履信、黃周、震東來訪,震東余曾極力推薦其入民報社,而受春木等之反等﹝對﹞,萬俥遂不敢採用。他於一月前入於《昭和新報》矣,觀其意頗怏怏之色焉。」此後10月16日,連震東亦曾拜訪過林獻堂,但所談為何?不見記載。
林獻堂的記敘,顯然與連震東的口述不太相吻,與吳濁流的聽聞亦有所不同。日記必然有所取捨,林獻堂多少隱蔽了某些情況。明顯者如「誇口無禮之言」究竟為何?多次來訪所談為何?便未見記載。至於不在文字之內的,就更難說了。所以,我們也沒辦法說林獻堂的記敘,便是事件的真實反映。但稍做對照,連震東的說法卻頗啟人疑竇。首先,他稱自己因中日文俱佳而招致謝春木等人忌妒一事便令人難以理解。謝春木等人反對是事實,但曾就讀東京高等師範的謝春木,又何嘗不通日文、中文?可謝春木早已在1952年投向中共,並於1969年去世。距離連雅堂的年譜出版(1975),已是六年之前,謝春木不可能與之對質、反駁。連震東的說法是否往自己臉上貼金?我們也就不得而知了。
若此事真如連震東所言,那麼為何連橫沒有為自己加以辯駁呢?鄭喜夫的年譜中並沒有交待。到了兩年後,他的外孫女林文月在《青山青史》中,承繼了年譜中的說法,並進一步補足了連橫沒有辯解的原因。林文月解釋:一來是該文雖是冒名,但確實出自連橫之玩笑;二來「則已略知此背後有人想要阻止震東進入報社。這種事情雖是委屈冤枉,但如果撰文筆戰起來,怕是只有越說越不清楚;況自己年紀已大,而震東方出道,它不願因自己樹大招風,反而害了兒子的前途,於是只得默默忍氣吞聲。」這樣的說法何來呢?在序中,林文月自道寫書時除了參考了年譜、著作等史料外,也訪問了連橫的親友。也許,這是連震東的親口說明也不一定。但第二個理由,看起來卻頗為牽強。如不澄清,不就更增加民報人員對連氏的誤解,怎麼會有利連震東呢?而且,連氏父子居然連親見允諾說項的林獻堂也未曾說明,不免怪哉。
當然,也可能連氏父子曾經對林獻堂說明原委,但林獻堂不僅沒有記載日記中,亦執意要令連雅堂除名。不過,林獻堂曾經允諾交與連家兩百元,以助連震東之學業,應該真的認為他「頗可造就」。而據日記所載,此後與連氏父子間也仍有往來,似乎並沒有加以疏遠。是故這一方面的猜想,可能性似乎不高。
連氏父子後來為何離開臺灣前往中國?連家後人與外界之間,說法自然也有所不同。但無論何者為是,連家顯然並非是參與當時那些「間接射擊」,力圖以促進中國革命以達到解放臺灣目的的抗日運動。到目前為止,除了抗戰後期,1944年連雅堂進入國際關係研究所服務,與這些臺籍抗日運動人士始有直接接觸以外,後來更參與接收工作以外,我們還看不到任何有力的證據表明連家確實在中國投入臺灣解放運動。但,憑藉著連雅堂的詩文與連家和國民黨要人的交游,連氏民族氣節之名盛於一時。
今日,我們翻閱連橫的作品,確實可以看到不少感時憂懷之作。據年譜所載,連氏也曾在《臺灣民報》發表批評時政之議論。一個心懷故國的連橫,彷彿可以藉此躍然紙上。而林文月的《青山青史》,便是如此為祖立傳。但同時,連氏也曾經為總督田健治郎做諭告翻譯,甚至曾為兒玉總督作〈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一首。這些行為,似乎與「愛國文人」的形象不符。而就《臺灣通史》的作序爭議一事,如果說請田健治郎等政要作序,是如連雅堂友人黃潘萬所言,乃為使日吏有所顧忌,不為干擾故。那麼具官方色彩的《日日新報》主筆尾崎秀真、《臺南新報》主筆西崎順太郎為之作序,又何故僅為林文月所稱「日本有識之士對《臺灣通史》其書之重視,以及對連雅堂其人欽佩」?
儘管連家人最後到了《昭和新報》任職,但在此一親日的報紙創刊時,連雅堂也曾在《臺灣民報》上為文批評該報為「御用報紙」。到底連雅堂的認同與節操如何?是否如香港媒體人賈葭所言,「周旋於日人與國民黨之間,其言行,日人及國民黨人均只見其一面」?又或者受生活所迫,有其苦衷?
那一個在日人殖民下的傳統文人連雅堂,究竟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又如何在其中自處?
儘管史料歷歷,略為索來,卻令人感到迷惑。
三、
收音機平板的講話傳來,鏡頭轉明。幽暗的空間中,一個男人正在拈香祭拜。燭光照亮了他的正面,成為畫面的焦點。婦人分娩陣痛,傳來陣陣呻吟。產婆循循善誘,不一會,判斷即將生產,令人準備水以便接生。男人方祭拜完,對此似乎無可插手,只好走到灶腳,對著正在舀水的女人喊了一聲:「腳手卡緊ㄟ」。女人應答。男人無可奈何,轉身飲水。一會,電燈忽放光明。男人抱怨了一聲,將圍繞著電燈的黑罩掀開,離開餐廳。不久,在一聲淒厲的叫喊後,嬰兒哭聲傳出。空無一人的餐廳,白色明體的字幕浮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
宣佈無條件投降
臺灣脫離日本統治
五十一年。
林文雄在八斗子的
女人,生下一子
取名林光明。
許多人或已認出,這是侯孝賢著名的《悲情城市》的第一幕。那平板的聲音,便是所謂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也就是終戰詔書。據說那一天,帝國境內的許多臣民,對天皇那言以正音,夾雜古語的演說一時無法理解。天皇的演說用語曖昧,廣播的音質也差強人意。但人們在當下,或者不久之後,很快便明白了那段話所要傳遞的,正是日本戰敗投降一事。
林光明,也是在這樣的理解下被命名的吧。寄盼戰後生活,能夠迎來光明。正如同不必再受到戰時需求、燈火管制而斷電,乃至遮蔽的電火一樣。
然而隨後迎來的,卻是一段苦澀而曲折,幽暗的記憶。
四、
珠江口。另一個四方匯聚之地,清帝國最早割讓的殖民地分峙東西兩岸。這裡的人們,直到90年代方才脫離殖民地身份。香港學者羅永生面對這曾經身處其中的殖民經驗,做過許多討論與批判。在一篇論文之中,羅永生試圖透過電影,窺探殖民經驗所烙印的香港政治無意識。他認為,殖民經驗使得香港人的身份曖昧不明,這樣的曖昧帶來的焦慮,呈現在香港臥底電影裡之中。一部部臥底電影,折射出港人不同時期的身份政治狀況。而對近20年來臥底電影影響最深的,便是九七回歸。羅永生如此論道「九七大限」的意義:
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著繁雜多樣的總總「過去」(pasts),並無清晰線索,然而九七「回歸」,卻逼著所有人去面對和接受一個一統版本的歷史命運。在「線性歷史觀」下所描畫的「歷史」長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歸」,但這卻非意味為人們找到了一個原鄉式的「歸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時間「大限」,毋寧是一個逼在每個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選擇。無論是走還是留,都要同時整理過去,為自己選擇未來。也正因為九七是這樣一個具存有論意義上的選擇(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個叫每個人都重整記憶,清理舊帳的大決算,仿如一個讓每個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關。
「重新做人」,這話聽來似乎過於沈重。人怎麼樣輕易的放棄、塗抹、批評自己的過往,而為了一個新的秩序,改頭換面,徹底與過去之我決裂呢?但回顧1949年以後的中國,幾波政治運動下,多少人被迫自我檢討「學習不夠」,批判自己過去的言行,只為了「跟不上黨的思想」,無法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重新做人」?這樣來看,「重新做人」卻也太輕薄,何以承擔過去總總的殘忍與沈重?
而這一切「做人的標準」,從來都掌握在權力者的手中,成為一種專斷的政治忠誠判準,左右著芸芸眾生的命運。如同日本帝國一面高唱天皇赤子、一視同仁,一面又以民度未開為由,合理殖民地的差別待遇。面對殖民者的兩面話語,殖民地人民受制於權力的網羅中,難以脫身。舊的認同已被隨政權轉移而無所憑藉,殖民者新的標準卻遙遙不可及,人們的身份也只得在其中游移,處於半途中端,不得為人的尷尬。如何擺脫這尷尬呢?一些人固守舊認同而拒斥巨變;另一些人則依循新標準,依盼統治者的恩澤;還有一些人,則尋求超越或迴避的可能性。
連雅堂究竟是那一種人呢?又或者,他也不只是一種人?在政治語言的攻防中,似乎不再有人關切。恰似柯文哲的父祖是如何面對皇民化運動下對教員的總總要求,又怎麼樣看待自己作為公學校教員這個身份?而他的學生、鄉里又如何看待他?對許多人來說,這些問題似也都無須探究了。
1945年之後,「做人的標準」又再次改易,這一切曲折的生命,都被放入了粗糙的「皇民」框架之中,只因為他們曾經在皇民化運動下,自願或被迫編入了「皇民奉公會」,或者擁有了日本名字。即是民族運動代表的林獻堂,也曾被南京政府懷疑其忠誠。他們,被新來的統治者鄙棄,因為統治者認為他們沒有在殖民統治數十年後,繼續保有漢民族的認同,反遭日人「奴化」。他們,不符合新的「做人」標準。
光明的期待由此落空,而過往,也得化為幽暗的記憶。
1945年的「生死大關」,並不只落在臺灣。隨著日本帝國的戰敗,東亞無數的人民陷入了「重新做人」的困境。那是在佔領區下生存,卻被接收者指為漢奸的人民;那是在殖民地中生存,卻被光復者指為皇民的人民;那是隨著皇軍的挺進移出,戰敗後孑然一身,回國受盡貧困歧視的日本人民。那是在新舊政權之間徬徨,而被專斷的權力宰割身份的人民。
近70年後的2014年11月16日,已經被人們淡忘的「臺灣光復節」後三週,連戰一句「青山文哲」,令人驚覺,原來,臺灣從未真正「光復」,而時間,也從未跨過1945年。這不是制憲國大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後,對國府感到失望之餘,寫下「臺灣暗復」那種「新生臺灣」的失落與悲涼。而是由自一個「半山」後代,對自己父祖輩的殖民經驗毫無認識與反省,也毫無考慮如何使這片土地上不同的生命經驗能夠彼此訴說與聆聽,無意——或有意的複製著殖民體系的話語。對照著連橫的生命經驗之種種,其孫連戰這一席話中,傳達出的惡意與無知,令人不敢置信。那是對在無情歷史洪流中徬徨無助,奮力求生的生命——連橫可能便是其中之一——沒有一點認識、同理,乃至同情而出的權力者的話語。我們不禁想問,假使連氏沒有在1930年代前期西渡投靠黨國,是否也得面對同樣的命運?而連家的後人,又會怎麼面對自己先祖的「青山青史」?
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得連戰講出這樣的話語?
這種權力者的話語,彷如日本殖民者再次回到臺灣,對著臺灣人說道:「你們這些清國奴,何以成為我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連雅堂、柯世元,「你們這些清國奴,何以成為我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五、
在《湮沒的輝煌》中,收著一篇散文〈寂寞的小石灣〉。夏堅勇為之感到寂寞的,並不是小石灣的乏人問津,而是據說埋骨於此的閻應元。那年乙酉,閻應元在江陰抵抗清軍,固守八十一日,壯烈犧牲。而這樣的粗人,在史書上,在文人心中的位置,卻不比文采風流,一日失揚州,尚待清軍容其成節的史可法。
夏堅勇為之不平。
趙衍慶有幸,在這一陣風暴後,得到了許多媒體的採訪,儘管是藉由他人之手記下,但也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了見證。這些隨軍來臺的小人物,固然沒有閻應元的英勇事蹟,但他們的經歷,我們又何以能夠冷漠呢?
趙衍慶有幸,他與中國史百年無數的災禍擦身而過,似乎也無須面對「重新做人」的認同困境。但他也逃不了連雅堂、柯世元的命運,得任憑人們就他留下的隻字片語,加以詮釋。於是兩位許先生或說他是新的「政治正確」下失語群體的一份子;又或者以他的案例,推演成「當年國民黨軍沒有也不會要未滿十六歲的小孩,以及女性去當兵」。
相比這些一時不察的小錯誤,《聯合報》社論的政治解讀更為離奇。不僅有著與江先生原文一樣的方法毛病,更將嚴肅的轉型正義歷史責任,共同體如何可能的問題,簡化為政治權謀下對執政黨的醜化。
想想,也不能怪罪今人。人們總是想要透過這些「真實的經歷」來理解一個時代,但不僅經歷是否真實,有待考驗;時代在人們生命中,留下刻痕早是不盡相同。一個趙衍慶,濃縮了一段歷史;但走進趙衍慶,卻看不到歷史的全貌。而歷史既與認同密不可分,也就無法逃脫於政治認同操作之手。我們永遠無法使過去的歸於過去,凱撒的還諸凱撒。
但每一個歷史的代言者都應該謹慎小心,不致使歷史失掉了它應有的重量。
否則贏得了政治,卻失去了歷史。人們,也就不得不斷的「重新做人」。
六、
青山如故,已然發生的事情,不會改變。過去的一切存在,自是存在,不因我們今日的種種行動而改變。
青山共賞,它不會,也不能壟斷在史學者或探訪者的手裡,因為過去本是社會的存在。人們總是不斷的藉著吸收記憶,試圖尋找自己在歷史之流中的定位。它必然被人們不斷的討論,也在人們的討論中不斷的變化身形。那些變化,或源自對事實的塗抹,或來自視點的轉換,或者,來自時間的無情。這一切,使得真實的過去彷彿如煙,形影雖在,卻難以把握。
儘管如此,青山依舊如故。
我想起《悲情城市》,想起其中的種種暗喻與明喻,在電影中,一樣有著不變的青山,那一彎山路黃石滾滾,山壁幽幽,一同見證了小城的喜樂悲苦。而我又想起聾啞無語的林文清:他是時代的見證人,以攝影為業,但卻不能說話,最終捲入反抗運動之中,隨之被捕,不知去向。電影也隨之走向尾聲。
也許,過去的真實就像林文清一樣,它不說話,卻真實的訴說著。而我們得如阿雪、寬美那般,在旁靜靜陪伴,從其向我們透露的簡短語句中,逼近其所要表達的一切。甚至,可能需要我們的代言。
而它也許要我們加以守護,以免政治力量的粗暴毀滅。
但,陪伴與守護從無身份的條件,
只要真誠與謹慎。
延伸閱讀:
有關連橫形象的變遷,或者「造神」,政大傳播學院院長林元輝舊作〈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有簡明而實在的析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1期(1998),頁1-56。但林教授這篇文章較無觸及認同問題,筆者在此希望呈現的,是那一個時代的臺灣漢人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共同的身份認同困境,以及在面對多層累加的歷史—地緣政治結構(1895年甲午戰爭、1930-1945年十五年戰爭、1927-?年的國共內戰,以及1947-1991年冷戰)的今日,如何認識這個困境的問題。不過順著林教授文章的思路,亦可檢討香港學者羅永生「奴性與殖民」的命題。見羅永生,〈殖民主義:一個迷失的視野〉,收於氏著《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3-13。
(2015年8月22日補述:今年初曾藉連橫家書進一步探索此問題,發現林元輝的論述頗有問題。例如林元輝將「阿膏」當作「阿片」,但事實上前者是一種中藥材。林元輝的描寫過於負面,有以論代史的狀況。)
有關「反共義士」的研究近年來頗多,但其中作者曾採訪在世「反共義士」者,筆者所見有以下三篇:
儘管學界已有一定成果,但不可否認的,對於這些如今已80多歲的老兵,我們的關注與了解恐怕仍然遠遠不足。
寫在後面
在這篇文章寫成以前,已經有管仁健與Mattel(許建榮)的文章談過連橫的「鴉片有益論」,這些批評大抵襲自林元輝的論文。筆者較不認同這樣批判的、只呈現一面的討論方式。其原因一是每個人物都有多面的樣貌,這種強調負面形象的論述本質上是一種反論述(counter discourses),旨在打破黨國塑造的愛國的、進步的連橫形象。但這種反論述並無法引領我們進入那個時代,從而更深刻的理解連橫。例如管仁健攻擊連橫「戀童癖」,但在古代中國雛妓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女子的成婚年齡也比現在早很多。承襲漢文化的連橫似乎也不例外。筆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能夠讓更多人理解歷史的複雜性與多面性,而非以單一向度來衡量、評價歷史問題。
文章寫完之後,另一位歷史普及作者 Emery 也在關鍵評論網上發表了討論「皇民化運動」的文章,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一併參看。
雖然筆者在書寫時,曾希望把這個議題放到一個比較大的脈絡、架構下來思考,但最後仍就是功力不足,一些面向沒有做好。文章存在過於福佬中心的問題,不僅沒有討論到原住民族面對日人文化制宰的情況,對於戰後來臺的「外省人」著墨也不夠。但如果那樣寫下去,這篇文章就會不只是9000字了。有關原住民族面對日人文化制宰的問題,讀者如有興趣,可以進一步參考Baliwakes(陸森寶)的個案。